程铁良
氟:卤族元素之一,有臭味。氧化能力极强,具有剧毒和强烈的刺激及腐蚀作用。微量的氟是人体必需的,而过量的氟将会对人的牙齿、骨骼、肾脏、神经系统、甲状旁腺、血等造成损害,导致氟中毒。
泪酒贵州
1991年12月底,我出差贵州,说起来,那是一件极偶然的事情造成的。
一年前,我拆阅大量的读者来稿时,突然发现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下肢变成不规则畸形的人向其他人诉说着什么;另一张是两个孩子的腿一个呈X型,一个呈O型。其惨状令人不寒而栗。
照片摄于贵州省织金县新寨村,那里的一些人由于受煤烟污染,患氟中毒,从而导致了一种氟骨症。
当地老百姓称这是“魔鬼附身”。
接到照片,我立即走访了卫生部地方病防预司,并于1989年12月9日在《中国青年报》第二版发表《救救新寨人》的报道,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披露。
时隔近一年——1991年8月,我再次打电话询问新寨氟病防治情况,卫生部地病司杜英同志介绍说,毕节地区氟污染问题仍没有解决,那里的人们饱受氟污染的危害,按照目前的防治速度,尚需数百年才能解决。
贵州怎么了?
带着满脑子的困惑,我登上了飞往贵阳的班机。
A.时间:1991年12月26日。
当我见到贵州省卫生厅地方病防治办公室主任杨大全时,没说多少客套话,递上了一份我起草的《关于治理毕节地区氟中毒污染的舆论呼吁的实施方案》报告,便问:“咱们什么时候下乡?”
刚刚从乡下回来两天的杨主任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50多岁。他倒也干脆:“明天。只要路不凌冻、雪不封山,一早出发。”
要过年了,如果没有这事,他肯定能和家里人过个团圆年。这下,让我搅了。


B.时间:1991年12月29日。
我们的“212”北京吉普车在织金县熊家场乡大树弯村的一间草房前停了下来。
昏暗低矮的草房里,53岁的刘德珍正抱着她一岁零两个月的孙子烤火。破烂不堪的床上,推放着一条脏兮兮的棉絮,在这里,她们一家人已经住了30年。
“身体怎么样?”我们问刘德珍。
看上去足有70岁的刘德珍说:“腰疼腿疼,牙也不好,已经干不了重活了。”
我们又查看了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牙齿,均是氟斑牙患者。她们不知道煤烟中的氟侵害了她们的身体,她们更不知道氟斑牙患者的牙齿将比正常人提前10-20年全部脱落,最后是骨骼变形、瘫痪、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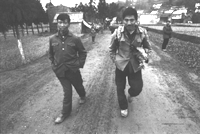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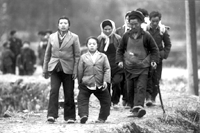
C.1991年12月30日
我们终于到了织金县新寨村。令人遗憾的是,新寨村的状况并没有因为一年前报纸登了那篇文章而改变多少。
走进荷花小学五年级的教室,我立刻被那难闻的怪味呛得大咳不止。经检查,这个年级13-15岁的学生百分之百都是氟斑牙患者。陪同我们采访的防疫人员感慨万分:“他们可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啊!”
49岁的吴道华从18岁开始腿就成了X形,他说这是风湿、天冷造成的。1986年普查时,医生说这是氟骨症,于是他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种病。
李发法今年31岁,但从12岁开始便不能走路了,双腿已成“Z”形,其父和外婆先后被氟骨症夺去生命。如今,母亲刘去秀也已经是混合型三度氟骨症,在家瘫痪10年。他的妹妹今年刚刚20岁,也因氟中毒失去劳动能力,一家人只能靠政府救济度日。
张怀芬,一个49岁的妇女,却在床上瘫了7年。她弄不明白自己的腿为什么不能伸直。我说我是北京来的,想给她拍张照片,她让孩子点燃了一盏油灯,那痛苦的眼睛里露出了一丝希冀,她用那浓重的地方口音对我说:“这么远,又要过年了,还来看我们,谢谢了。回北京,给我们讨个方子,我们这地方怪,得这病的人多。”
她掀起被子,露出干枯曲缩的双腿,让我拍照。
我只感觉取景框中一阵模糊,半天调不准焦点……
走了一家又一家,串了一户又一户。病人之多,境况之凄惨,令人触目惊心。
据统计,贵州毕节地区约有400多万人患氟斑牙,180多万人患氟骨症。1982年至1988年,毕节地区织金县对71988人进行普查,氟斑牙的患病率为59.7%。新寨村最小的氟斑牙患者只有两岁半。就连织金县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也未逃脱氟斑牙的恶运。
老百姓实诚。我知道,张怀芬即使躺在床上,也会记住有个北京来的人看过她,她肯定盼望着北京再来人时给她带来一付药方,让她站起来。
潘多拉祸匣的魔力
二十世纪初,一位口腔医生发现,氟魔能吞噬人类。实际上,早在10万年前,氟魔已经对人类产生危害。我国山西省阳高地区的古代“徐家窑人”就患过氟斑牙,这种灾难曾载入我国晋代稽康撰写的《养生论》中。
氟魔,给世界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氟魔所到之处,侵蚀了人的骨骼、神经系统和肾脏,把人推向死亡。
研究表明,氟,广泛存在于矿石、土壤、水、植物、动物、调味品、酒及大气中,氟是地方性氟中毒的致病因子,当人们长期摄入过量的氟时,就会引起氟中毒。
氟病病区的类型主要有三类:饮水型、煤烟污染型和食物型。根据目前的报道,我国氟病主要是饮水型和煤烟污染型。而后者在世界上还只有我国存在。
根据1988年以来的普查,我国除上海外,均有地氟病流行。饮水型和煤烟污染型氟病人在3.3亿人,涉及1187个县。也就是说,全国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1人生活在高氟区。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县上坑村,有220户,总计1314人,一口土井含氟最高达9.12毫克/升,氟魔危害该村400多年。1984年普查,氟斑牙患病率91.6%,几乎家家都有卧床不起的氟骨症病人。
在河南洛阳市,所辖9县2区除伊川、宜阳尚未查清外,其它县区均有氟病患者。全市水型氟病村1425个,煤烟污染型602个,受害人数373万多,已患病人数167万多。
吉林省15个行政县(市)的2900个村屯成为氟病区,病区人口1445142人,患氟骨症62113,患氟斑牙近60万人。
我们再回到贵州,看一看我国独有的煤烟污染型氟中毒的情况。
贵州省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由于是无烟煤,当地老百姓取暖做饭习惯于不用烟囱敞口烧煤,煤中大量的经燃烧被释放出来,污染了空气,侵害了人的身体。此外,贵州地处山区,秋冬季阴冷潮湿,玉米和其它大秋作物收获时常阴雨绵绵,为防粮食霉烂,当地人常用敞口炉火烘干粮食和其它食品,潮湿的粮食和食品强烈地吸收煤燃烧地释放出来的氟,造成二次污染,使氟中毒进一步扩散。
1987年,贵州省社科院扶贫工作队来到威宁县石门坎乡。当他们踏上这方土地时,那随处可见的畸形肢体的“怪人”着实使他们震惊了!扶贫工作队写信给贵州省委办公厅信访处反映这一情况。很快,省、地、县地方病防治部门联合组成调查组,对石门坎乡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的结果触目惊心。
石门坎乡共有4863人,氟中毒患者近4000人。其中患氟骨症的病人竟占一半,几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据当地群众反映,凡20岁以上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节畸形,40岁以上就不能上坡干活背水,活到60岁以上的人不多。
该乡全部人家祖祖辈辈居住土结构草房,无窗,通风极差。各家烘好的粮食中,含氟量比未烘干的要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空气氟也比使用非敞开式灶地区的空气氟高出十多倍。
王正英原本一家五口人,丈夫六年前患氟病症致瘫后死亡,她本人也患中度氟骨症,双上肢活动功能受限,关节轻度瘫形。三个孩子分别为10岁、8岁、7岁,10岁及8岁的孩子双下肢严重瘫形,双上肢轻度瘫形。他们身高都在一米以下,四肢短小,面黄肌瘦,严重发育不良。
关于威宁县石门坎乡地方性氟中毒问题,1946年有一位英国传教士曾作过调查,还运走了一具氟骨站晚期死者的尸体,进行研究。同时以石门坎134例氟斑牙和4例氟骨症病例为论据,写了一篇《中国地方性氟中毒》的文章,在英国的《柳叶刀》杂志发表。遗憾的事,自那以后的30年,国内外医药卫生界对石门坎的地方性氟中毒,再也无人过问。
煤烟污染型氟中毒,遍布我国14个省市,以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最为严重,受危害人口近5000万,现有氟斑牙患者4000多万,氟骨症患者260多万。
这就是现实。
现实迫使我们清醒起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攻学界还未找到一个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治疗氟中毒的办法。于是,人们把目光集中在预防上。
饮水型氟中毒的预防,是从1965年在吉林省乾安县打成第一眼低氟深机井后开始的。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90年,国家、集体、病区群众为改水共投入资金97697万元,共建成各种改水降氟工程设施25858项。
预防煤烟污染型氟中毒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改炉改灶,变敞口炉灶为封闭炉灶并加上烟囱,把有害气体排到大气中去经大气稀释,减少危害。
一切似乎很简单,改水降氟,改灶排氟,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是的,真理永远是最简明的。但要实现真理却非易事。
谁是上帝
对于煤烟污染型氟中毒的发现,远比饮水型晚得多。然而,它却得到党和政府高层人士的重视。
这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
早在1976年6月,贵州省医学院、贵州省环境卫生监测站、毕节县卫生局组织了医疗卫生、地质专业等几家单位的50余名工作人员对毕节县吉场区东方红大队8个生产队的地方性氟中毒进行了调查。1979年,贵阳医学院魏赞道教授在《中国预防医学杂志》刊文,报告了贵州省地方病食物性氟中毒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宝山等对我国西南地区非水源型氟中毒进行研究,提出氟中毒病人过量摄入的氟不是来自食物而是来自于燃烧的煤。
1981年,湖北恩施卫生防疫站对湖北鄂西州氟中毒病人进行调查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1985年,三峡工程提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议事日程。三峡省筹备组主任李伯宁在调查三峡工程上马后的移民迁建问题时,发现涪陵、万县、黔江、宜昌、鄂西州等地的居民同样为氟中毒所困扰。
李伯宁如坐针毡,强烈的责任心驱使他要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反映上去。
于是,由他牵头,拍了一部电视录像片,给国务院及各部委领导观看。
这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
有人替他捍了一把汗,说:“这样的片子给中央领导看,领导们会不会指责我们丑化社会主义。”
但是,中国毕竟不是那个时代了。人们在充分审视自己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后,变得更加理智。录像放完,在场的人谁都不想多说话,震惊,使他们仍沉侵在那一帧帧不可思议的画面中,每个人心中都多了一个问号:解放近四十年的中国,竟有这等事情,可能吗?
1985年4月,国务院召集九部一委会议,对三峡地区煤烟污染型氟中毒的情况进行研究。会议决定,责承卫生部和农林部联合组织专家调查组。
1985年7月,联合调查组提交一份调查报告,不但证实了录像片所反蚋的总是真实无疑,而且现实生活比录像片提供的材料更耸人听闻。
国务院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再次召集各部委领导研究决定,由各部委分担筹集1000万元作为氟中毒防治科研经费。最后,落实了600万元。
1986年,三峡地区开始进行改炉改灶试点。
从1976年开始的对地方性氟中毒调查算起,到改炉改灶试点工作进行,整整经历了10年!
这次试点向15万户推广了改进的炉灶。
至此,三峡煤烟污染型氟中毒的大规模集中防治暂告一段落。
但是,问题没有解决,三峡地区,毕竟只推广了15万户,对于受煤烟污染型氟中毒威胁的5000万人口,我们怎么办?
答案还是只有一个:改炉改灶。
然而,谈何容易。
A.体制的羁绊
卫生部地病司地病二处专门负责氟病防治的同志。讲起六七十年代的地方病防治来,一脸的畅快。
“那时候办什么事都比较容易成功。因为有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乌兰夫、陈锡联、李德生都曾担任过组长。由于层次高,每年开会都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986年机构改革后,领导小组撤销,施行行业领导。机构改革后,有20多个省仍保留了省委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也有一些省归口政府部门。上海、山西、福建等则放到卫生厅或爱卫会。由于卫生厅无法调如水利、轻工、商业、财政。交通等部门的工作,结果这项工作1990年又归到省政府管。”
“再往上,难度就大了。卫生部无法指令或协调财政部拨款,更无法让水利部去打井降氟……工作非常困难。”
说到此,他沉默了,显得无可奈何。
B.防治经费哪里来?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后,全国性的地方病监测、科研、宣传、培训又成了一新的问题,经费由哪里出。
1991年5月,卫生部地病司起草了一份申请当年地方病防治经费的报告。经费总预算230万元,遗憾的是至今仍没落实。
那么,地方病地方管得了吗?
贵州省安顺地区每年用于改灶经费多是告省地病办下拨的专款。从1985年至1991年,省拨专款每年在5万至10万元之间。该地区1985年至1991年改炉改灶6476户,仅占需改灶户数的2%;按目前仍需改灶户每户补助30元计,共需经费943万多元,加上宣传、会议、仪器购置等,尚需1100万元。如按每年省拨专款最高的10万元计划,现有炉灶全部改完尚需100多年!
这还不足令人吃惊。毕节地区五年来已改灶5500个,仅占需改灶户数的万分之七;这里年人均收入只有217元,而改一个灶就需60—70元,每年省和地方财政拨款的防治经费只有三四万元,照此下去,解决氟污染问题岂不今事越千年!
C.老百姓观念难改变
在采访中,我们所到的地方,有些已经改灶的农民家里又改烧了明火。他们认为,明火散热量大,比封闭炉灶暖和。
看到这番情景,我的心情难以言喻。几十年的传统习惯,加之对科学的麻木冒昧,使本已举步维艰的防治氟中毒工作更加雪上加霜。
D.地方防疫人员不足,设备奇缺
1985年2月25日。贵阳花溪宾馆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地方病领导小组组长李德生同志听完贵州省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负责同志的汇报后指出:“消灭地方病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仅靠你卫生厅长(指贵州省卫生厅厅长曾国珩)、卫生部门不行。必须要各部门紧密配合……在地方病防治、科研工作中,要充分发挥专家和业各技术人员作用。专业队伍要相对稳定,并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
话是这么说,但做起来可就难了。
在毕节县一家小酒馆里,毕节县防疫站一位工作人员向笔者倾诉了满肚子的牢骚。
“谁都知道搞氟病难,费力不讨好。咱们今天跑的沙田乡野拉沟,上沟只有19户人家,总共119人,氟斑牙100%,氟骨症70%。今天记者看到了,走到上沟要两个多小时。谁愿意跑?”
“氟病防治经费少不说,即使是普查了,改炉改灶了,服了药了,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见效的事。氟中毒不是急性病,短时期内又死不了人,哪一届领导也愿意干立见成效的事,像这种病,投入多,见效慢,谁愿意干!现在我们科,就我一个人搞氟病。毕节县这么大,我管得了吗?”
1991年12月30日,织金县防疫站出动了一辆破得已无法再破的旧式救护车,到城关镇花红村拉上25名村民进行X光检查。霏霏细雨中,汽车倒像个拖拉机,缓缓地向前蠕动。
织金县地方病防治所所长高儒清张开他那一口的氟斑牙说:“条件就是这样,但工作还得做。我们这代人得了病也就算牺牲了,但我们不能再让下一代得病。”
人们在寻找,寻找出路和办法,寻找制服氟魔的金钥匙。
理想与现实
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常常构筑起一座理想的大厦。对于未来的描述,总会使们激动不已。
64岁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环境卫生与卫生工程研究所的曹守仁教授面带微笑接受我的采访。曹教授从1987年开始,带领一支科研小组对有关防治氟中毒的三个课题和13个分题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曹教授兴奋地说:“目前国内外都在研究治疗地方性氟中毒的办法,但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把高氟水降为低氟水的地区,经过10年观察,不但氟斑牙患者减少,而且氟骨症奇迹般地发生了逆转。目前,我们对蛇绞石治疗氟骨症的效果正在进一步研究之中,如果取得突破,将是对整个人类的一个贡献。如果经费充足,我们再干上个四五年,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
然而,理想和现实,毕竟还存在距离。
1989年,曹守仁带领的课题组写了一份题为《室内燃煤污染氟中毒的防治》的报告。世界卫生组织环境规划署的一名官员和西太地区环境保健中心主任郭鸿铭看了以后很感兴趣。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专家审评,认为很有合作价值,并基本同意投资支持研究煤烟污染型氟中毒——这一仅中国存在的问题。
于是,一份关于联合国开发署援助开展《室内燃煤污染氟中毒的防治》项目的申请报告经卫生部地病司正式递交经贸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
谁知,这位老同志不久离开了岗位,一位接管的新同志认为,把炉灶安个烟囱通到室外不就可以了吗,有什么必要立项?于是,项目申请被取消了。
WHO西太区环境保健中心和环境规划署没有接到中国官方的项目申请报告,自然无法申报援助经费。1990年,该中心拨款1万美元,列了四个题目,课题组又补充调查,以充分的理由和材料,说服有关人员继续向联合国开发署申报。1990年3月,课题组将申请报告再次通过卫生部递交经贸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无奈,报告又重蹈覆辙!
1991年,WHO西太地区环境保健中心又拨款5000美元,希望再做有关工作。64岁的曹守仁教授有些灰心了,奔跑了这么长时间,他实在没有能力去搞公关,于是又回到实验室里闭门搞起研究来。
也是在1991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不得不向世界银行贷款10万美元,用于这项科研。
直到今天,曹教授仍弄不明白,有关人员为什么不为自己国家的事情着急!
中国有3亿多人受到氟中毒的威胁。生命,为它在健康状态下的延续,而呼唤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心。
这篇文章既将结束的时候,举国上下又一次掀起打击伪劣产品、维持产品质量的新高潮。我不禁在想:维持生命的质量,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吗?
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有很多比治氟更复杂、更艰巨的工作,只要重视,只要真正下决心去做,也做成了。比如甘肃通过并已经实施的禁止呆傻人生育条例,中国大面积开展的扶贫工作……
今天,面对3亿多中国人和他们的后代,我们必须拿出治理氟中毒的科学、有效的规划,我们不能在生命的呼唤面前麻木、彷徨了!
(本文刊载于《三月风》1992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