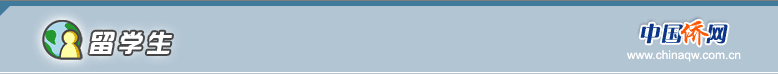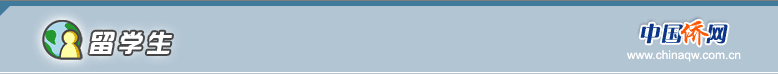|
野狗身世
都说家狗是驯化狼的产物,可又有谁在乎过野狗的身世?
从凶恶的野狼到温顺的看门家,从人见人怜的家狗再沦落成无人认养的野狗,它们会重返暴戾吗?
直到来到保加利亚,我才知道了这个答案。
苏东剧变,激进的经济改革像一场无声的风暴,悄悄地先是刮走了厨柜里的奶酪和香肠,然后是面包和牛奶。
生活越来越困窘,日子越来越揭不开锅,主人忍住伤痛把饥肠辘辘的爱犬赶出家门,推入社会。
被主人放逐了的狗,白天围着街边垃圾箱游转,夜间在寒风冷雨中哀号。同样在街头流浪的吉普赛人用乞讨所得的零碎钱买来面包和香肠,喂给比他们更饥饿的狗。
从此路人多了一个施舍对象。街头流荡的狗越来越多,人们从嘴边省下一点点零食,抛给小心翼翼跟在身后的狗,还有人会把晚间吃剩的骨头包好,好在第二天上班路上丢给狗啃。
于是,被私人抛弃的家养狗顺理成章地成了众人养护的流浪狗。阴云渐散,经济日见好转。当地人更加善待这些特别时期受到特别痛苦的种群。居民们常买来鲜肉给近处流浪的野狗吃,狗最喜欢光顾的地方是公共汽车站这样人流聚集的公共场所。
阳光暖洋洋的照在巴尔干的大地上,野狗们懒洋洋地睡在水门汀的步行道上,没有人会惊扰它们,它们与人类交流的眼神是温和的、安然的。
它们或许还在期盼着老主人把它们领回去,或许早已适应了街头生活,已经把大街当成屋、把路人当成主人了。
有日我忍不住问一个保加利亚女孩:为什么困难时期竟然没有人吃狗肉呢?
她平静地说,东正教徒不吃狗肉,狗享有动物权,它一样拥有生存权。
教徒服从于宗教的约束,宗教规则调整个人行为模式,对于这些,我不奇怪。但当一个群体饿得发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保持对屋上的飞禽、屋内的猫狗不动一点点歹念,那就不只是宗教的禁忌所能克制得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深处,早已把狗当作生命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吃了它们无异于吃自己的兄弟姐妹,此心何忍?扪心而想,当人类本身饥饿的时候,狗也一样在遭遇饥饿的痛楚,它们何曾对人类无故龇牙咧嘴、甚至以人肉来果腹呢?
我又回想到国内。几年前曾在《重庆商报》上读到的一则新闻,内容叙述了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广场值勤的一个管理人员,“果断”地处决了一只与主人走散了的幼犬,原因是这只临时“野”狗可能要咬人,还可能在广场新铺的花岗石地砖上制造拉屎拉尿等不卫生事件。
我一直在想,可能要咬人和可能要拉屎拉尿这样的“轻罪”真的给我们提供了正当性和合法性,足以谋杀这只曾给人们,至少是给主人以欢愉的狗吗?连稍微与主人拉了点距离成了临时野狗的小动物命运况且如此,那些被主人遗弃或真正与主人长期失去联络的野狗,它们的命运岂不是更糟糕?野狗在我们国度里是没有位置的,它们没有前世也没有后世。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我们的文化根子里,命贱如条狗,平日被主人呼来唤去,稍不遂意,常遭一顿拳脚,打死了还要剥皮、烹煮。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豢养宠物犬,有些人爱狗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这些仪态万方的宠物犬,能给人类注入待动物的新理念,抑或只能促使传统观念更加恶化?当人类对某些动物大搞特权,而对某类动物大搞歧视之时,人类在野狗的眼里充其量是只被狗放逐了的野人。(来源/神州学人,作者/石渝)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