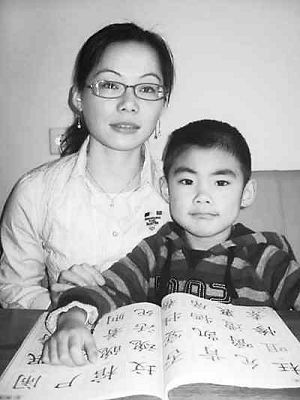
汉语作为儿子的母语,从咿呀学语言开始,他已经接受了以儿歌和古诗词为先的启蒙教育,沉淀了如《满江红》、《归原田居》、《将进酒》之类的汉语字音的记忆。“背如反掌”这句口头禅常作为我们对他记忆字音的赞赏和再接再厉的鼓励。汉字是音形义的组合体,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识字教学方案来展开中文教学常常引起我的思考。
有幸的是我所在的荷兰丹华学校于2007年9月开始开办《中华字经》的教学课程。先进的教学理念,新颖的教学方法让我不但认识到“识字无难易,写字有简繁”的识字规则,并明确了“背字经,记字形”的教学目的,制定了“定量学习,定期复习”的教学计划。在子旭4岁时,我坚持了正确的教学方法,坚定信心,一边实践教学,一边等待预期教学效果的出现。
《中华字经》中无一字重复,并以四字一句的韵文形式把众多的汉字组合起来,读起来朗朗上口,这对儿子来说,就好像回到当初学习诗词时那种“重温旧梦”的感觉,既亲切,又喜欢。加上CD/VCD和会说话的学习机的相伴,着实让他兴趣盎然。每次我和他都要在40分钟内贯穿32个字经的认读,进行逐句分读,整体连读,接龙游戏,冥想记忆,音形对应,单字认读,紧张而又富有挑战的教学程序。为避免认读的单调与枯燥,需要和着不同节奏的拍子,力求诵读富有活力和节奏感,再加上用手指点读来加强大脑对汉字的音形对应的记忆。儿子读累了就放放CD“悦耳”一番。最后还要把刚学好的字经在熟悉的儿歌如《小星星》旋律中唱出来,在轻松、充满情趣的气氛中结束一次的学习。
温故而知新,我非常重视定期复习,按计划要求子旭在一个星期内有3次复习,达到巩固记忆的目的。字经的每日必修,逐渐地使他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兴趣和习惯成了他持续学习字经的动力。有时甚至当我忙得不可开交时,他还能主动借助学习机自学字经呢。
在遵循“读字音记字形,讲义先靠边”的新教学理念下,子旭在4岁到5岁的10个月时间里完成了4000个汉字的学习。在认读的过程中为了能增强记忆字形的意识,我增加了汉字基础笔画、部首、字形结构和独体字、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等汉字类型的教学,而孩子对字义的理解将随着学习时间的增加而循序渐进,知识面的扩宽和阅读水平的提高将水到渠成,字经的这个教学理念与老庄的“无为而为”的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
子旭凭着他《中华字经》第一阶段的学习效果,开始了每日一篇的《水平阅读》,现在已阅读了160多篇。他对这些故事性强的文章很着迷,现在可以整篇通读,识字率达95%。在阅读时碰上那些记忆模糊的汉字,他会先画出来,在我的指导下重新读字音记字形。在学字经和阅读中,我针对音近字、同音字、多音字、形近字容易产生混淆的问题,对儿子进行有侧重地归类教学。如“残”,在我提示字音后,让他在所学过的字经句子中记忆搜索“残”字和与其音近的字。他能先后说出:“坑蒙孕残,嫦妞妩婕,叼吃饥馋,谄媚狡猾,菩萨忍常,渴饮品尝,资产累计,敞释矛盾”等。然后我把“残”字拆分和重组部件,出现了“钱浅贱溅践栈盏”,在明白不同的义符各自趋向的意义后分别组词,明确了各自读音后再联想字经的句子,这样横纵扩展交替地练习,加深了他对汉字的印象。还有字形歌,在字形结构基础上把一些字体相近的字加以归类识字,例如当我告诉他“融”字读音后,引申出了“触、解、懈,蟹”:以“昆虫的角是触角,牛角当刀来解开,心底解开就松懈,螃蟹像虫地上爬”,见形解字,达到形义教学的效果。
现在5岁的儿子已经在丹华学校四年级学习,他对汉字的认识从《中华字经》过渡到《水平阅读》,整个过程加强了他对汉字字形、字音的识别能力。随着阅读量的增加,他对中文的理解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华字经》和《水平阅读》密切配合,相辅相成,达到加快儿童识字教学的目的,实现了由量向质的跨越。(宋雅真,寄自荷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