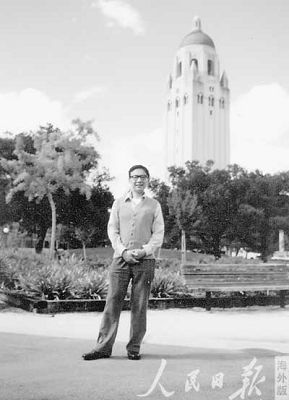
回忆起30年前的那个冬天,许卓群总想写点什么留作纪念,但每次提起笔,都感慨万千,不知从何说起。
当年在美国走下飞机那一刻,许卓群惊呆了: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照亮大地,高速公路上车流像银河般流淌。他不禁感慨:“要是在有生之年看见中国也有这幅景象,该多好!”
30年过去了,许卓群的愿望正在变成现实,这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奉献和努力。
最难过是口语关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许卓群开始学习英语。他有预感,不久的将来中美关系会得到改善,他也许有机会到美国去学习计算机,而一旦到了美国,首先要过的还是英语关。刚到美国时,对许卓群来说难在口语,每个月要考试一次,开始不及格,3个月后就达到七八十分了,但他还是觉得听外国人讲话有些困难。
在美国,和各国学生一起学习口语,许卓群第一次接触到了美国的课堂教育方式,他十分赞赏。他认为,学英语除了按照常规背生字、学课文,小组讨论也很重要。学习期间,他喜欢主动加入小组讨论问题,“这样能把原来被动学习的词变成主动使用的、灵活运用的词语。”
为学好口语,许卓群还有自己的办法。他记下英语书的各种句型,学习时将不同的词放进去练习,许卓群认为这样做对专业知识学习和工作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在学校里和教授讨论问题时都常常使用这些句型。
虽然在美国生活了两年,但是提起英语口语来,许卓群还是有点“怵”。他风趣地说:“只要外国人一开玩笑,我就听不懂了。”
落后促使人奋进
在华盛顿学习英语时,许卓群也在考虑自己申请去哪所学校学习。他原想去麻省理工学院,因为他知道麻省理工学院有位教授也在研究他在国内从事的PETRINET和微程序研究。然而到了美国,许卓群才得知微程序设计已经完全转化成了产品,大学里已不再研究。研究PETRINET的人已很少,在麻省理工学院搞研究的教授也去了别的学校。这时许卓群感觉中美之间差距太大了,在信息方面好像和美国隔着一座大山,从杂志上了解的情况都是几年前的东西了。
最终,许卓群选择了到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学习计算机操作。第二年他转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要学网络和数据库技术,这在美国也是刚开始不久的新事物。“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网络,通过网络接触到什么是计算机,什么是电子邮件。”许卓群虽然在国内有基础,但到美国后,他果断地改变研究课题,从头学起。
一边学习,许卓群一边收集资料。他想,北大还没有一本像样的教材,一定要多带些有用的资料回去。
在美国,许卓群遇到过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在美国第二年,他从纽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到达后发现行李不见了一个,后来失而复得,但箱内有一摞厚厚的东西不见了,其他东西却丝毫无损。后来回想,许卓群觉得可能是美国有关部门觉得箱子里折叠厚厚的纸张很奇怪,所以打开查验?其实那只是一些挂历,是一位北大教授托许卓群带的待送的小礼品。后来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
回国的时候,许卓群带回了几大箱资料。“其实很多资料后来并没用上,但当时就是想尽可能多带些资料回国。”许卓群提起此事不禁笑了。
回到北大后,许卓群立即给学生上课,学生们求知若渴,他的课很受欢迎。
扮演承前启后角色
直到今年,许卓群才真正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回想回国后这些年,许卓群认为自己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文革”期间学术停顿,“文革”后人才断层,青黄不接,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有所缓解。
如果当时不去美国留学,许卓群说他以后也会去,他认为到国外去学习视野会更开阔。原来他不知怎样带研究生,到了美国他知道带研究生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导师自己要做研究,二是要帮学生选好选题,这是很关键的。在美国,导师本人是非常努力的,相当多的老师上午9时上班,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都不回家还在实验室。
许卓群很欣慰的是,现在北大和国外很多学校签订了合作协议,每年送出一批教师去做访问学者。无论是像他们那样已经有了研究成果再出国,还是到国外读学位,他认为都是大有裨益的。许卓群说:“我亲眼目睹了旧中国的贫穷、落后,也经历了新中国的蓬勃生机和不断发展壮大,值得我为之出把力。”(周小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