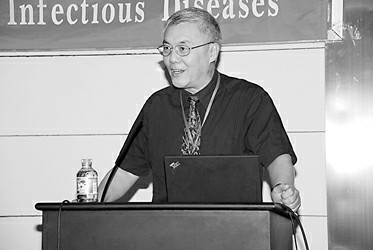

——微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赵国屏的“改革开放30年”
30岁那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改革开放的大潮,将正在农村插队、当着大队书记的赵国屏,带入了正规的生命科学研究的大海。从此,他的人生轨迹,与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轨迹紧紧交织在了一起。
从考取复旦大学生物系、通过CUSBEA计划赴美求学,到出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首任副院长,再到就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和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今年正好“花甲”的赵国屏最为欣慰的是,自己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做成了。
“设计人生”,对80后年轻人热衷的这个词汇,赵国屏说:“我们这代人,从来没想到过设计自己的人生。我们只是结合自身的能力和兴趣,不断地去适应国家需求,为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
三十而立:“做农民做不到的事情” 高考被复旦生物系录取
1969年,20岁的赵国屏离开上海的家,去安徽蒙城插队,带着一种轻松感。
他的父亲赵祖康,是中国公路泰斗,国民党政权最后一位上海市代理市长(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规划建筑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去蒙城农村,他不仅摆脱了周遭歧视的目光,还可以满足搞生物研究的愿望。
“中学时看到《科学画报》上有篇介绍DNA双螺旋的文章,感觉生命太神奇了。从此,我就下决心要考北大,学生物,但是,‘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我上大学的梦。”赵国屏那时的想法很单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他,感到粮食太重要了,“我小时候自己做过嫁接育种,我也崇拜电影《艳阳天》里带领农民生产自救的肖长春,那时我真是想去改造农村”。
6年后,这个在农村经历了各种磨难锻炼的知青,从城里的“乖孩子”成长为大队书记。他在为困难户解决吃饱饭的同时,依然憧憬:“我的大队,生产水平要与美国相当。”
他领导的大队专门有个农科队,有几十亩试验田,从育种一直做到推广。建小油坊、办小工厂,建学校、推行计划生育。他要把一个淮北的穷村,建成“变江南”的实验室。而他的未婚妻俞自由,更由知青当上了蒙城县委副书记,名动一时。
1978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了中国。赵国屏的心热了,但他依然放不下改造农村的“实验”。这时,一位生产队长对他说:“虽然你现在做得很好,我们也需要你;但是,你应该多学本领,做农民做不到的事情。”
于是,赵国屏参加了高考,志愿是复旦大学生物系。他被录取了,分配到微生物专业。当时班里同学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15岁,他30岁,排在第三。
读书期间,他写了一封针对农村问题的信,得到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的赏识,并得到中央领导批示。此后,他以学生身份成了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虽然担任过从班到系、校的各级学生干部,赵国屏的4年大学生活,始终在刻苦学习、培养研究素质中度过。
当赵国屏毕业的时候,他担任班长的微生物专业班被评为上海市三好班级,学校希望他留校,当一个兼做行政工作和教育科研工作的“双肩挑”干部。
又一个选择放在了他的面前。赵国屏想,要做研究,就要集中力量,踏踏实实,从头做起;他决定要坚定地走一条漫长的“科班之路”,于是考上了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的硕士研究生。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分子生物学教授吴瑞向中国教育部建议: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发展很快,中国要尽快培养这一领域的年轻科技人才。为此,他向美国近百所一流大学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说服它们接收中国留学生,促成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从1981年开始实施。赵国屏以他优异的成绩和英语水准,获得植生所的推荐,顺利通过了CUSBEA的笔试和面试,远赴美国普度大学,开始了留学之路。
“我上大学之后,读遍了所有专业课的英语教材,为的是以后做研究有用,但就是没有学过TOFEL,因为从没想‘考出国’。但是,CUSBEA给了我真正的机遇。”赵国屏至今感念这一次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