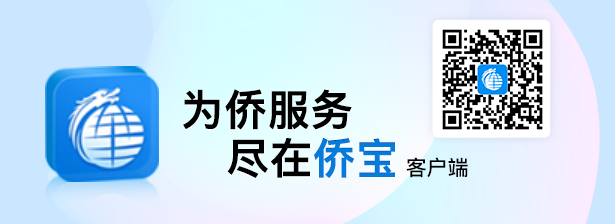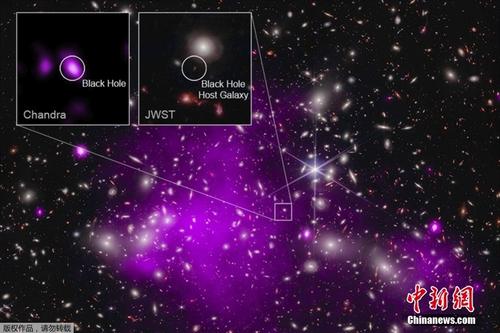“侨”这四十年:坎坷岁月的悲歌和喜歌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广大海外侨胞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华投资的先行者和主力军,是中国面向全球、扩大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华侨华人功不可没。
“‘侨’这四十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后,海内外投稿纷至沓来。即日起,一篇篇佳作将陆续刊出,展现华侨华人与中国同行的四十年。
——编者按
坎坷岁月的悲歌和喜歌
刘登翰
一簇火熖在我眼前忽闪忽闪地飘动,这是从几千里外的家乡带来的祭奠的纸钱燃起的火熖。火熖随着纸钱的不断添加哔哔剥剥地响着,晃动的火苗中仿佛有个人影闪动,这是谁呢?是父亲来看望当年他还不懂事的儿子吗?
1948年,父亲再度踏上远行菲律宾的航程,本以为一年半载就要回来的——这在我们家族已成规矩,男丁十六岁或小学毕业,就要出洋去谋生,然后回来结婚成家,再返赴南洋。此后一年两年就这样往返一次,像把一条细细的丝线系在远远飞去的风筝上。没想到这次由于时局变动,风筝线断,父亲阻隔在菲律宾几十年,最后连一把骨殖也埋在那片异国的土地上了。
父亲的音讯渺无,母亲独自撑起这个有四个儿子的家。
1955年夏天我从厦门师范毕业,被要到厦门日报当记者,总算可以多少帮到母亲一点。记者生涯的开始,我跟一位老记者跑文教线,有时到厦门大学采访,我从囊萤楼宽大的走廊走过,里面正上课,我故意放慢脚步,聆听教室里传出的讲课声,心里有些不甘,都一样年纪,为什么我不能上大学?
翌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动员在职干部报考大学。周围条件适合的同事、同学都争相报名,我也动了心,却不敢说。倒是母亲先看出来了,对我说,你若想读书就去报名,别担心家里。就这样,报社放了我半个月假复习,1956年9月,我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
毕业分配,我申请回到厦门以便帮助母亲照顾三个还在读书的弟弟。如愿回福建报到时,却发现在人事局的分配名单上我那一栏的备注多了几个字:“海外关系复杂”。我被发落在闽西北,一晃就是二十年。原来还葆有一点温馨记忆的父亲,成了我的包袱,这个无所不在的“海外关系”,无论怎样也甩不掉。
历史又迎来一场巨大的变革。受惠于这场变革,改变了我生命的轨迹。我从一个基层打杂的文化干部,回到年轻时候向往的学术岗位。那年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却对人生充满了疑惑。年过四十要像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学子一样,从零开始进军学术,其困难可以想见。不过,这是我四十岁以后才重逢的春天,我不能辜负命运的这一赐予。母亲在天上祝福的眼光,会一直慈爱地陪伴着我。
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是受到信任、受到尊重、也让我有以报答的一页。我从1979年岁末调入福建社会科学院,至2008年岁末我72岁才退休。但退休并非研究工作的结束,三十多年里我出版了三十多部著作,也获得了国务院给予的专家特贴、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授予的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奖章和奖状、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政府评予的“福建省优秀专家”荣誉,学术上也获得一些奖励。这些本都微不足道,晒出来只不过想说明,作为一个华侨子弟,我的前二十年和“这四十年”,有着天壤之别。
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这四十年”,就没有我一个默默无闻的华侨子弟生命重光的四十年。
当年连想都不敢想的父亲,又时时在我梦中出现。虽然父亲于1962年——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就过世了,但我常想,在他病危的时候谁伴在他的身边?他久羁异邦重又结婚留下子女没有?那是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啊!他们现在的生活怎样?我什么时候才能到父亲坟前尽一份人子之情,洒一杯祭奠之酒,代为母亲和我们四个兄弟表达数十年积累下的思念和哀悼?
我庆幸能有机会两次应邀到菲律宾出席学术会议,都在马尼拉。会议之余到处打听“纳卯”在哪里?那是我自小从母亲口中知道的父亲在菲律宾谋生的地方,在我心里,纳卯和父亲是连在一起的。在会议发言时,我曾半开玩笑地说:我到菲律宾,有一半是来“寻根”的。朋友们都很热心,告诉我纳卯是远在菲律宾南部的绵兰老岛的首府,一座近两百万人口的菲律宾第三大城市。在华侨口中的纳卯,即今日著名的达沃市,距马尼拉乘机还有两个小时的航程。会议行程紧迫,且杳无一点线索,无法前往,只能拜托寻找纳卯的朋友帮我打听。然而拖了几年,并无结果。
2010年,我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活动,适逢家乡南安刘林刘侯旅外宗亲会成立,我也是南安刘林的刘氏子弟,同宗刘再复知我来香港,便转告他弟弟、宗亲会创会会长刘贤贤邀我参加庆典仪式,把我选为宗亲会的名誉副会长。在与宗亲们闲聊中,我说起父亲远赴菲律宾,埋骨纳卯,却一直不知墓在何处,无法前去祭拜。宗亲会一位副会长刘清池先生说:没关系,只要有你父亲的名字,我们可以帮你找,菲律宾有很多我们宗亲会的机构。果然,一个多月以后,清池叔从香港给我来电话,说找到了,你父亲就葬在纳卯的华侨义山。原来是清池叔在纳卯的弟弟刘清枝和几位宗亲,拿着父亲的名字,到华侨义山密密麻麻的坟冢中一座一座去査对,终于找到我父亲的墓葬。
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我百感交集,不知是悲是喜。为先人祭扫,这本是极寻常的一件事;可对于许多如我一样的亲人远离而不知所终的华侨后人,却需如此周折;所幸我还能找到最后这点音讯,不知尚有多少妻子儿女,翘首天边,永在无望的寻找和等待中!
获知父亲墓葬消息的当年万圣节(这是西方相当于中国的清明节),我即携同妻子飞往菲律宾,经停马尼拉时,菲律宾著名华侨诗人云鹤(蓝廷俊)和他的妻子散文家秋笛(也是南安刘氏的宗亲刘美英),说在纳卯他有个姑妈,要陪我们同行给带带路。我们搭机从马尼拉飞抵纳卯,步出机场,就受到前来接机的二三十位宗亲的欢迎,还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布横幅。清池叔的兄弟刘清枝也特地和另一位宗亲,带着子女从“山里”开了两个小时的汽车赶来纳卯。我再次感受到异邦逢故亲的那份温暖。住宿是云鹤的表弟提前安排的,晚餐由宗亲会宴请,接着几天的餐饮也都由宗亲们安排。那些天,我沉浸在亲人们热烈而温馨的无限深情之中。
祭奠在第二天上午进行。万圣节刚刚过去几天,华侨义山又迎来一群人。父亲墓碑上端画着一个十字架,他入乡随俗信了基督。可我们依然按照老家的方法为他祭奠。除了我们远道带来的祭品外,宗亲会和云鹤夫妇也都准备了香烛纸钱。火焰越燃越旺,影影绰绰仿佛父亲的影子、母亲的影子都聚在一起。几十年的等待,几十年的哀思,几十年悲悲喜喜无处倾的锥心的话语,仿佛都在这烈烈的熖火中宣泄出来⋯⋯
到达墓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已有几束鲜花供在父亲坟前,显然有人来祭扫过了。谁呢?是父亲在纳卯留下的妻子儿女,抑或是其他亲戚故旧?弄清这个谜,成了我们祭拜之后的又一宗心事。
匆匆在纳卯住了三天,无处打听消息,只得抱憾回程。离开前,我给义山管委会留下一封信,那是写给我尚未见面的菲律宾母亲和我可能的同父异母兄弟,请义山管委会若有他们的地址或消息,一定转交,信中留下了我在中国的详细地址和各种联系方式。
然而一年、两年,终无回音。
正失望中,偶然的一次聚会,突然又柳暗花明。
那时我已从福州退休回到厦门。我们本是个大家族,祖父生有八男二女,除了年岁和我相仿的八叔,其他都谋生在菲律宾,祖父抗战胜利后归来不久,这个大家庭才拆散开。至今留在厦门尚有九十多岁高龄的大伯母、从南洋回来的五叔、与我一样因年小未及出洋的八叔和排行老四的父亲四家,子辈孙辈近百人。每两年一次的春节聚会,散枝开叶的亲人们从国内、国外回来团聚,虽不能全到,每回也要席开七、八桌。有一次香港回来的两位堂弟,讲起七十年代刚到香港时,曾到纳卯探望当时尚还健在的他们的父亲一一我的大伯父,听说了父亲一点情况。父亲过世后留下三个孩子,大的五、六岁,最小的尚不满两岁。伯父接济过他们,但一个弱小女人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实在无法在城市生活,只好卖掉少少一点家产,搬到山里去。后来小孩长大了,曾回来感谢伯父, 伯父过世后,联系就少了。
渺茫中总算昐到一点消息。拜托伯父在纳卯做旅游的二女儿一一我的堂妺代为联系,她人脉广,又热心,很快就联系上了。父亲再婚的菲律宾妻子已经过世,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吃尽艰辛,总算成人,或开店、或办厂、或谋职在私人企业,发展得都还不错。
大团圆的日子终于来了。得到消息后,2015年的万圣节,三弟和我女儿(我临时因病退了机票)先去纳卯一趟,约好纳卯的三个弟弟见面,一起为父亲扫墓。在纳卯,三个弟弟的热情接待,虽之前未曾见面,却是早已心心相通,有着血脉相连的那份浓浓情意。临别前,相约在2016年春节家族团圆的聚会上再见。在香港的堂弟也发出邀请,让大伯父留在菲律宾的几个子女,也带看他们的后辈一起结伴同来,共聚这个美好的节日。
这是一支多达29人的浩大队伍,从菲律宾专诚飞来,为了一份心愿:认祖归宗。团圆席上大家披上一条鲜红的围巾,显得热闹吉庆。之后,我们到鼓浪屿寻找曾经住过的老家,那里已成了一处著名的园林式咖啡厅;我们在中山路一栋临街的骑楼前留影,父亲在厦门最后的住处已成了步行街热闹的商铺;我们回到家里一起学着揉面擀皮包饺子,像儿时的游戏一样把饺子捏得七扭八歪;我们还在书房里摊开笔墨纸砚,教弟弟们用毛笔写自己的中文名字⋯⋯几千里的山高海远,几十年的亲情阻断,仿佛只在一瞬间就都化解,心贴心地感受到彼此的温情和血脉的搏动。
分别的时候我们再相约,和伯父家的一起,趁万圣节再去纳卯为先人扫墓。
这回是从厦门出发飞往纳卯,浩荡荡也是二十多人。扺达的那晚,两家合在一起宴请,七八十人,一个个介绍,还是记不住。我为每家各写了一副对联,那是南安刘氏家族字辈排序中的两句:“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父亲和伯父都是“园”字辈,我们兄弟则是是“翰”字辈。这些对纳卯的亲人或许一时还弄不懂,但留下来就是记忆,留下来就是传承。
伯父和父亲的墓地都在华侨义山,相距不远,一道祭拜之后,两家便分开活动。在纳卯几个兄弟陪同下,我们游览了纳卯的名胜,早年西班牙到来时遗下的古迹,还乘船到一个小岛野餐和游泳⋯⋯临别时大大爆涨的行李装满了菲律宾的土产。我们行程中原有在纳卯祭拜后转机去宿务薄荷岛游览的计划,五弟(纳卯三兄弟的老大)知道后连忙带着太太和女儿搭下一班飞机赶来,陪我们在那里享受热带的阳光、晚上清凉的月色和潜泳中观赏热带鱼群的惊艳⋯⋯只有亲人才有这样的周至;只有这样的周至,才能弥䃼被无情岁月分割的那份烈烈的痛和深深的爱!
一场伟大变革,中国打开国门,重新走向世界,“侨”字连着一带一路,变得宏阔而博大。这四十年里,有多少悲悲喜喜的故事。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的家庭,抑或整个世代的海外华侨华人和他们留在祖国的亲眷,岁月烙在每个人身上和心上的印记,都在见证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在怎样的阵痛中诞生、成长和辉煌!
【作者刘登翰,曾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已退休并卸任。现为厦门大学两岸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福建师大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