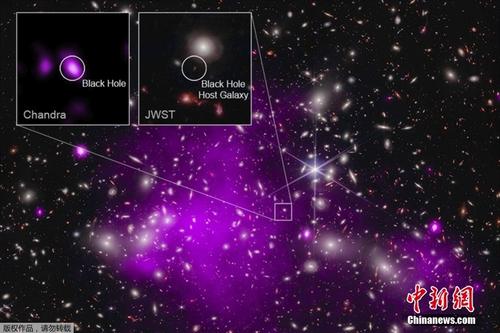在特莱津,他们曾绝望地依恋着一个世界



我想去看看特莱津的,不仅仅因为它曾经是集中营,还因为特莱津被解放后,人们在煤堆下、阁楼里,找到了4000多幅犹太儿童的画和一些诗歌。
那是关押在这里的犹太艺术家、学者、老师带领孩子们创作的。
这些作品的存在,就像我最喜欢的这幅画所表现的:在无边的黑暗中,月亮与星光仍在闪亮;在风暴肆虐的大海上,帆船仍在骄傲地前行;在时光之剑指向的未来,有永不熄灭的烛光……
我要独自离去
我要独自离去,去到一个地方,
那里的人不一样,他们更为善良,
那个地方很远,谁也不知道在哪儿,
在那里,一个人不杀死另一个人。
也许,我们更多的人
一千倍的坚强,
就能达到这个目标
在为时太晚之前。
注:写诗的女孩叫阿莱娜,16岁的时候被关押到特莱津,幸运的是,她活到了特莱津被解放的那一天。
知道特莱津,是从林达翻译的《汉娜的手提箱》和她写的《像自由一样美丽——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上。
这个小镇离布拉格60多公里,原来只有5000左右居民。1941年10月,占领捷克的德国人将居民强行迁走,特莱津变成了德语的“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关押、转运犹太人的集中营。特莱津前后关押过十四五万犹太人,其中包括15000多名儿童,他们当中只有一百多个孩子活下来。

埋在煤堆下面的作品
特莱津从来就不是旅游热点,网上也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攻略。从布拉格出发的火车不到特莱津,需要到Bohusovice下车再换汽车。看上去,特莱津比想象中还要偏远一些。
从Bohusovice火车站到特莱津,有三四公里的路程。犹太人当年被火车送到这里后,是提着行李走过去的。据说,一些到特莱津参观的人,为了体验当年犹太人的感受,也会走过去。
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集中营博物馆门口有画着黄色大卫星的牌子:MUZEUM GHETTA。这是一座黄色的三层楼,我们在一楼花215捷克克朗(约60元人民币)买了特莱津的全票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10点半将会播出当年纳粹拍的宣传片。
是的,纳粹拍的宣传片。当年纳粹为了迷惑世人,为了应对国际舆论和国际红十字会的视察,谎称特莱津是“模范集中营”,是犹太人自治的小镇,还拍了这部叫做《一个作为礼物送给犹太人的城市》纪录片。镜头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在踢球,看到了老奶奶在织毛衣,看到了妇女们在种菜,甚至还有男人在演奏音乐,即便做了如此之多的粉饰,仍能看到营区的住宿是如此的拥挤,看到人们木然的表情和绝望的眼神——失去自由,人们的眼眸也就失去了光亮。环境可以造假,但是谁能为那么多人造出眼眸中的光亮呢?
楼上的展品,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除了孩子们的画(还有许多画在布拉格犹太区平克斯教堂的二楼展出)、诗歌,还有他们做的布偶,以及自制的演出服装。
哦,不要以为这里真的是歌舞升平。那些关在这里的犹太艺术家们,对自己的未来并不抱希望,但是他们相信总有孩子能活下来,他们利用一切可能偷偷地给孩子们上课,抓住一切机会(比如国际红十字会来视察)让孩子们可以画画、写作、唱歌和演出。囚徒21855号、作曲家汉斯·克拉萨,就让孩子们排演了自己进入集中营前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儿童歌剧《布伦迪巴》。《布伦迪巴》在特莱津一共演出了55场,其间,一些孩子被送往了奥斯维辛,别的孩子再替补上来。1944年10月16日,汉斯·克拉萨也被送走了,死在毒气室中。
我无法想象,那些孩子们是怎样在集中营歌唱的,孩子们的歌声对于他们自己,还有那些成年犹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伊凡·克里玛,捷克著名作家,是在特莱津开始学习写作的,他记述当年的情况时说:“我被挤在其他观众中间,听得如醉如痴。我看见许多人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和我一样想要哭泣。这种经验完全令人沉醉……”
那些犹太艺术家、学者、老师们,知道自己给予孩子的绝不是写作、歌唱、绘画的技巧,而是活下去的希望。就像克里玛说的:“一个孩子只有绝望地依恋于一个世界,一个童话的世界,在那里善的力量将最终战胜恶的力量。……这种信念帮助我们支撑自己,得以在羞辱、忧虑、疾病和饥饿中幸存。”
孩子们的作品为何能保存下来?原来,有个孩子的父亲是铁匠,是集中营中唯一会打马掌的人,这个孩子后来被允许住到父亲的铁匠铺子里。他们就把画埋在了铁匠铺的煤堆下面……
那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
离开集中营博物馆,我们选择先去奥里河对面的The Small Fortress,即小要塞。
特莱津始建于1780年,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约瑟夫二世为了防御北面的普鲁士人而建的,历时10年建成后,国王以他母亲玛丽亚·特莱希娅的名字命名。1882年,人们又在河对岸修建了一个小要塞,叫做“克莱·费斯屯”。后来要塞变成了监狱,因枪杀奥地利大公而引发一战的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就瘐死在这里。
这是一片政府设立的公墓,墓地上树立着高高的十字架和大卫星,墓碑上有编号。我们不知道这里一共有多少个墓碑,也不知道墓碑下是否真的埋葬着殉难者的遗骸或骨灰。我猜想,这片墓地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吧,一种祭奠与纪念、控诉与铭记的象征。
每一块墓碑旁,都有一丛玫瑰,许多鲜红的花朵绽放着。墓碑上有编号,有些有名字,有些没有。许多墓碑上放着小石头,那是前来祭奠的人们放下的。
我把手里的花,放在583号墓碑上。那是一块没有名字的墓碑。我不知道它代表的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孩子还是一个老人;是死于饥饿、疾病还是酷刑;是1942年1月被绞死的16个犹太人之一,还是在1943年11月17日那个从清晨站到深夜,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上厕所的“点名”之后倒地的300多囚徒中的一个……
我们在特莱津参观的最后两个地方,是特莱津的太平间、葬礼大厅和骨灰堂。当我们冒雨来到这个没有人迹的地方,壮起胆子走进深深的隧道,骤然间看到大厅深处被灯光照亮的巨大犹太烛台时,真的是被震撼到了。
没想到在特莱津会有这样一个充满犹太宗教与文化习俗的殡仪之所。在这个半地下的建筑中,有一条拱形走廊,走廊墙壁上的文字大概是犹太教的经文,两侧的房间很像陕北的窑洞,里面分别停放着当年运输遗体的车子、整理遗体用的床、简陋的棺木和一些似乎是石灰制成的骨灰盒。一间屋子的墙边,有红砖和石灰砌的墓,上面的墙上有逝者的名字,我注意到,他们很多并没有生年,只有逝年,如1942,或者1944。
我猜想,这个犹太殡仪馆应该是特莱津最初改建时犹太人建的。最开始,德国人还不敢把许多国际知名的犹太人都杀了,但又需要把他们都控制起来,于是德国人对捷克的犹太领袖说,要为他们建立一个犹太人自我管理的城镇,只要他们“不制造麻烦”,就可以正常生活。于是,三百多位犹太建筑家和艺术家来到这里改建特莱津。来到特莱津的犹太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在自投罗网,他们仍然希望在这个只有犹太人的小镇上,尽可能地保留犹太人的传统宗教与文化。
但这个小小的犹太殡仪馆何以能够处理后来大量的死亡呢?短短的三年时间,就有33430个囚徒死在特莱津。克里玛曾说:“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我每天看到车上高高地堆放着可怜的尸体。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
最开始,死者还有一个木箱子入殓,后来就只能集体掩埋。据说纳粹最后修了一个一昼夜可以处理190具遗体的焚尸炉。
583号,我放一束鲜花在你这里。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曾经是一个人,一个和我一样,向往自由、安宁生活的人,一个喜欢蓝色天空和绿色大地的人。我希望你已经合上了自己的眼睛。
只有在梦中才能幸免的宁谧
小要塞黑白相间的粗条纹大门口,竟有一种很强的现代风格的装饰感。但里面一道门上的铁丝网,将人们迅速地带回到当年。门上的德语“ARBEIT MACHT FREI”,意思竟然是“工作给你自由”。
小要塞是集中营中的监狱,任何人违反了“纪律”,都会被送到小要塞。人们都知道,没有一个犹太人能活着走出小要塞。
最里面的院落中,一间间编着号的囚室排列着,有的里面还有当年的床铺、马桶、洗脸盆。几十个囚徒只有一个洗脸盆,几百个囚徒只有两个马桶。那些床铺虽然已经空了,但从床边的编号不难看出,那并不宽敞的床铺上至少要睡三个人。
令人奇怪的是,在一间大屋子里,我们看到整整一排白瓷洗脸池,看上去比大学宿舍中常见的还讲究。原来,那是为了应付国际红十字会视察而临时安装的,那条管道根本就没有接通。
最让我不寒而栗的,是两排关押特殊囚犯的小牢房,它们的宽度似乎不足一米,有些连窗户也没有。
窗户,对这些囚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事后我发现,在走进这些牢房的时候,我总是在寻找窗户,哪怕是很小的、被铁栏杆封死的窗户,我努力用镜头透过它们捕捉外面的光亮与绿色。我似乎承受不住那些黑暗、那些沉重的门和锁。
特莱津的幸存者,后来成为作家的克里玛,在《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中说:“我意识到自由的匮乏远甚于食物的匮乏。从集中营的窗户我只能看到遥远的山,我不能走出集中营的大门,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让我感到压抑。”
当集中营里的犹太成年人努力为孩子办起了一个学校(仅仅存在了几个星期),老师让克里玛写作时,他写了喀尔克林地,写了派特忍山(Pet?ín)的公园。他说:“我写树木而不写人,是因为我认识的人很少。每一个我认识的人不是像我一样的命运,便是消失在被战争吞没的世界里。树代表着自由。森林和一种仿佛只有在梦中才能幸免的宁谧联系在一起。”
囚室床上的一本书和一副眼镜
离开小要塞,我们重新回到河对岸的建筑群。在午后的阳光下,走过寂静的街道,来到一座很大的房子,从地图上看,这是一个由三层楼房合围的封闭空间,里面有两个院子。曾经的犹太人自治委员会就在这个楼房里,所以这也是集中营遗迹一个很重要的展出场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成年人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似乎更加直接地反映了集中营的残酷现实。当国际红十字会来视察的时候,他们悄悄地把一些画塞在视察者的手中,让外界能够了解真相。
据说,孩子们最开始画画的时候,也画了很多集中营的情景和灰暗绝望的感受。但是他们的老师,杰出的女画家和儿童艺术教育家弗利德,让孩子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平和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幻想自由飞翔。她还带孩子到阁楼窗口,去看蔚蓝的天空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她知道,在如此残酷黑暗的环境里,在身体被囚禁的时候,就越发需要心灵的自由和想象力、创造力。自由与美,是任何邪恶的力量都不能战胜的。
这里,也有一间复建的囚室,那是一间不知道关押着多少人的囚室,几排三层床占满了大部分空间,床栏杆上挂满了囚徒的衣服。
在底层的床铺上扔着一本书,上边还放了一副眼镜。
他们从布拉格,从捷克的其他地方,从欧洲的不同角落被送到特莱津时,纳粹限定他们每人只能带25公斤的东西。但许多人将书带到了集中营,当时只有10岁的克里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把三本书塞进了自己的皮箱:改编的荷马史诗、狄更斯的《匹克威可外传》和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们》。他说:“这三本书在后来的三年半中成了我的精神食粮。”

这里,是否还有另外一处墓地
离开特莱津时,天在下雨,只好放弃了去特莱津城外的犹太人墓地和苏军战士墓地。
但我很想知道,特莱津是否还有另外一处墓地,一处德裔的墓地——在捷克被解放之后,曾经生活在捷克的大量德国人(在当时划定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版图之内,居住着上百万德国人,他们有的已经居住了几个世代)遭到了剥夺与驱逐,特莱津立即就变身为关押德国人的地方。在十多万被关押的德国人中,只有极少数是纳粹分子和冲锋队员,大多数仅仅因为他们是德裔,其中16000多名是十五岁以下的儿童。零星的记载表明,特莱津拘押德裔人口的初期,由于疾病、缺乏食物和非法的屠杀事件,关押的犯人死亡率极高。
1948年2月,在德裔人口被驱逐之后,特莱津集中营终于关闭了。但这一段“特莱津后传”却被隐藏了40多年,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捷克政府采取开放的态度对待历史上的民族恩怨,解禁了官方的档案资料。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代表捷克人民向在大驱逐行动中被屠杀的德裔捷克人表示道歉。1997年,特莱津集中营的展览终于添加了关押德裔人士的记录。(陆晓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