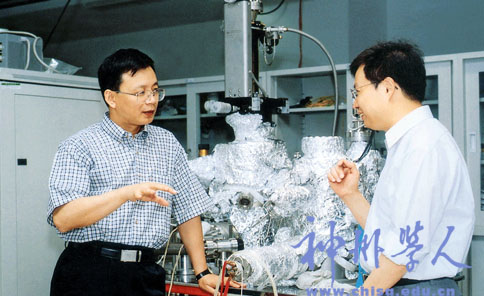
在科学的春天
2009年4月,浓郁的春色让安徽合肥从清新淡雅的传统写意画变成了浓墨重彩的现代写实油画。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校园里鲜见几座堂皇气派的新建筑,很多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建筑已显得有些陈旧。一座三层楼前挂着“欢迎少年班同学回家”的红色横幅,显然,那是去年中科大庆祝50华诞留下的痕迹。少年班的教室看起来和很多普通学校的教室毫无二致,如果不是刻意提醒,我们甚至会恍然置身于一所中学的教室。但校园里那些几代人熟悉的身影却以雕像的形式永久地驻足。梅贻琦先生曾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在这里,双臂环抱、面含微笑的郭沫若、静静沉思的华罗庚、严济慈、钱学森、郭永怀、钱临照……所有这些都在无言地提醒你:这是一所大师比大楼多的学校。采访时,正是清明节过后,每一座塑像前都有学生敬献的鲜花静静绽放,让一缕人性的光辉照亮心田。
树欲静而风不止,今天的中科大正在不动声色地运筹帷幄、招兵买马,准备打一场新时期的科技攻坚战,人才引进成为抢占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在一校之长侯建国院士的日历上,已经安排了一项重要日程——6月率队前往美国考察,主题很明确——人才引进。“对于优秀人才我们没有指标限制,理、工、文,我们都要,关键看水平,如果学校没有相应专业的,我们可以为他开设新的专业……”
2008年12月,国家出台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5所高校入选国家首批20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高层次人才引进再次成为国内不少大学校长们热议的话题。
虽然中科大在第一轮“千人计划”答辩中有5人顺利入选,与清华大学并列高校榜首。但地处合肥,中科大更觉形势紧迫。“科大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校最大的差距在人才,最缺的是战略科学家、教育家和学科领军人才。尽管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们要把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会促使我们在眼光上更高远一些,心胸上更博大一些,更进一步着眼全球、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哪怕实现这个目标要用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我们现在就要朝这个目标迈进。”
缘定中科大
“不要命的上科大”,这是上世纪80年代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但在福建福清长大的侯建国在高考前对这所学校并不了解,只不过他也是以一种“不要命”的劲头考进了中科大。
1977年,当在历史的长河中绕了一个大弯的中国重归理性和秩序时,高考成为一个重要的风向标。那时高中毕业的侯建国在福清的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工,师傅是全县惟一的一位八级钳工。在1977年的570万高考生中,也有侯建国的身影,但他未能如愿。第二年,师傅鼓励他接着考,侯建国说:“在复习冲刺时,我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实在累了,上班时就蜷在钳工床底下睡一会,需要时师傅就踢我一脚,我赶紧爬起来。”
填报志愿的时候,侯建国的第一志愿是福建农业大学农业机械系,重点大学他报了上海交通大学。他想,万一考不好,或许招生老师会看在他当过钳工的份上,同情他,让他有个学上。当他收到通知书的时候,看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8个大字时喜出望外,几乎每一个字都让他的心激动半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这样看了一遍又一遍,激动了一天又一天,半个月后,当他去买火车票的时候,才发现他要去的大学不在北京。遥远而陌生的合肥用辗转延伸了48个多小时的火车铁轨迎接了侯建国的到来。
在中科大,当同学们在不要命地学习,考CUSPEA的时候,侯建国却在课余时间徜徉于图书馆,文学、历史、艺术、哲学……能看的书都看,补充了很多数理化以外的知识。一个又一个同学远赴海外求学,进校时连26个英语字母还写错了两个的侯建国觉得那不是适合自己的路,他在中科大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成绩开始冒尖,基础也很扎实。读博士期间,国外的同学给侯建国寄来美元,他去报名参加了一次托福考试,成绩也过了,还联系到美国东部一所私立大学,找导师钱临照院士写推荐信的时候,老先生说:“这所学校我连听都没听说过,你还是别去了,等做博士后时再去不迟。”
1988年,正在读博士的侯建国意外地得到一次去前苏联科学院结晶学研究所做科研的机会,他的科研开始走向国际前沿。有国家的资助,没有生活压力的侯建国从容地和苏联的科学家们交流,吸取高水平科研的营养。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对于苏联的文学、艺术、历史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侯建国在工作之余跑遍了莫斯科的博物馆,看歌剧、芭蕾舞,那段时间,侯建国感觉“心情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