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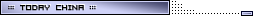
李玉霄简历
1970年出生于苏北农村,师范毕业后返乡,在乡办中学教语文。1992年初,参加当地的“社教”(全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乡村干部同吃同住(有的甚至成为牌友),大家一起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出谋划策”。办法都是上头给的,“一乡一业、一村一品”、“走出去、请进来”之类,包括往农民家的院墙上刷标语,在国道沿线树起大标牌。1992年年中,“社教”正欲全面推开,小平南巡讲话传达到了当地,一夜之间,队伍解散,“社教”戛然而止,我则成为县广播电台的编辑。自此,开始进一步熟识中国基层官场之种种怪现状。
1996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读研,1999年毕业,进南方周末,做社会新闻,跑过不少地方,但最多的是河南,那儿是我的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