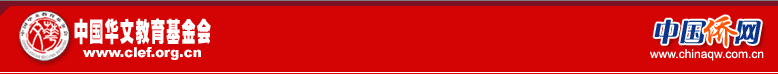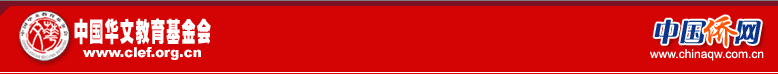|
老公的中文
文/于珈(纽约)
一切都是从“蟑螂”二字开始的。
那个夏天我们刚开始约会不久。偶有一次聊天,他说他也会一些中文。我大为惊喜,叫他赶紧说几句给我听听。他就发了“蟑螂”二字的音。我猜来猜去,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在他重复了四遍之后,我半信半疑地用英文说“莫非你是说蟑螂?”他非常高兴,说正是。我说你还会什么,他说就这些,别的不会了。唉,恋爱中的男人吹牛也不打打草稿,就这“蟑螂”两字也算“会一些中文”。
虽说是失望,我倒也好奇地想知道他为什么偏偏只会说这两个古怪的字,而不是人人都会的你好谢谢之类的。于是,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起了他的中文的第一课——蟑螂的故事。
一天他和他的一个同事在法拉盛的一家茶厅喝珍珠奶茶。没喝几口,他感到牙齿咬到了一个脆脆的东西,接着一股恶心的味道满口散布。他哇地吐了出来。找来茶厅服务生评理。机巧的服务生装作不懂英文,就给他来了一杯冰水,算是安慰。可怜的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旁边的一个好心的姑娘实在看不过去,就当地教他说了“蟑螂”两个中文字。于是茶厅里即时就响起了他的洋腔洋调的蟑螂蟑螂,闹得老板只得出面,他才算罢休。
在珍珠奶茶里吃到蟑螂这样的事情,我宁愿不要相信,毕竟珍珠奶茶是我的最爱。但是,委实从那以后,他是扎扎实实地记住了中文“蟑螂”二字。
随着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增多,他也多多少少跟我学了一点点一点点中文。大,小,高,胖,快,头,小孩,红,绿,诸如此类。要命的是,他总是忘不了他的“蟑螂”二字。无论学了什么中文字,总归要和他的“蟑螂”连在一起。于是,我们就有了“大蟑螂”,“大头蟑螂”,“胖蟑螂”,“又快又胖蟑螂”。“的”字他一直不能明白,也不大会用。
有一次,在我的一个朋友家聚会,我们一帮中国人聊到开心处,忍不住就母语直上,顾不得他了。后来他和朋友家的两岁多的女儿玩在一起了,听说俩人彼此互教互学中文。回到家后,我问他学了些什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神情如要登台一样认真,“Birdsare鸟鸟——,Carsare车车——,Dogsare狗狗——”尾音拖得长长的,嗲得和两岁的小女孩没有差别。我笑得流着眼泪捂着肚子。他被我笑得一头雾水。等我终于止住了笑,他一本正经地问我,中文里名词的复数是不是就是把单数的字重复说一遍。
我们订婚后,他向我请教怎么用中文说妻子丈夫,我就教了他“老婆”“老公”,并且告诉他这是比较随便比较口语比较亲昵的称呼。擅长于组词连句的他立刻来了一句中文“我是你的白老公,你是我的黄老婆”,“老”字发音还不准,听起来就象是“黄脸婆”。可怜的我,还没正式过门就成了人家的黄脸婆,“小蜜”“美眉”之类的词是万万不能教他的。
新婚伊始,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好歹随着他慢慢增加的中文词汇量,“蟑螂”已没有这么重要了。前不久,我们终于搬着住在一起了。他原来的公寓里蟑螂横行,他还慈心不杀。公寓楼里每两星期来一次杀蟑螂的,他总是把杀者拒之门外,他的公寓自然就成了蟑螂们的避难所。搬家搬到最后一趟的时候,他问我怎么用中文说再见。我说你终于想学有用的中文了,就非常认真地教了他“再见”,直到他发音几乎纯正为止。我们拖出最后的两个纸箱,他对着空荡荡的公寓,用几乎是字正腔圆的中文,深情地说道:“再见,蟑螂。”(来源/美国侨报)
|
|
|